一杯酒,饮下可以醉人,不饮则可以保持清醒。这一饮一不饮,一醉一醒恰是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。有人身陷杯酒之中,长醉不醒,双眼迷离离,心神恍恍然、神色晕乎乎,终日不知自己身处何处、心思何物,昏聩度日;有人置身酒杯之外,冷静客观,目朗神清,对自己、对周遭的事物都有较为清晰的判断,无论遇到何事都能做到处变不惊、镇定自若,似乎天塌地陷都不足以惊其神思、变其颜色。这两种迥然相异的状态所呈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饮酒态度,也是两种相反的为人处世方式,其中细处,值得神思。

杯酒之内与酒杯之外的不同状态,其实可以用一则典故中的两个人来做一个较为清晰的演示。如《隋书·牛弘传》记载:“弘有弟曰弼,好酒而酗。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,来还宅。其妻迎谓之曰:‘叔射杀牛矣。’弘闻之无所怪。问直答云:‘作脯。’坐定。其妻又曰:‘叔射杀牛,大是异事。’弘曰:‘已知之矣。’颜色自若。”隋朝名臣牛弘的弟弟牛弼好饮酒而且时常酗酒,曾经因为一次醉酒而把牛弘用来拉车的牛给射杀了,等到牛弘回家的时候,他的妻子早就在门口等候然后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牛弘。牛弘听到之后并没有表露出诧异或吃惊的样子,妻子再问的时候,牛弘又是干脆了当的一句:杀了做成肉干。等到牛弘坐定之后,他的妻子再次说起这件事情:小叔子射杀了牛,这是大事啊。牛弘还是不为所动,只说:我知道了。然后面不改色。

在这则故事中,妻子的大惊失色是有缘由的。一是因为杀的是牛车。在古代,牛有两种用途。一者是耕地,一者是拉车代步。牛作为拉车之用的历史由来已久,自汉代以来,由于马在战乱中被大量消耗,故而稀缺,《史记·平淮书》记载:“自天子不能具钧驷,而将相或乘牛车,”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,汉代初期即便是天子的座驾也很难找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,至于将相之类多乘牛车,自此便开风气,之后牛车便逐渐成为了清廉节俭和名士的象征,文人士大夫多喜欢乘牛车。而在古代,私自杀牛是犯法的行为。二是因为射杀的是牛车座驾。一般意义上,车架銮舆等同其主,冒犯天子銮舆等同冒犯君王,故而射杀车架已是大不敬。除此之外,牛弼的醉酒犯浑不必多说,只是一次古今常见的撒酒疯。唯一值得一说的便是牛弘的镇定自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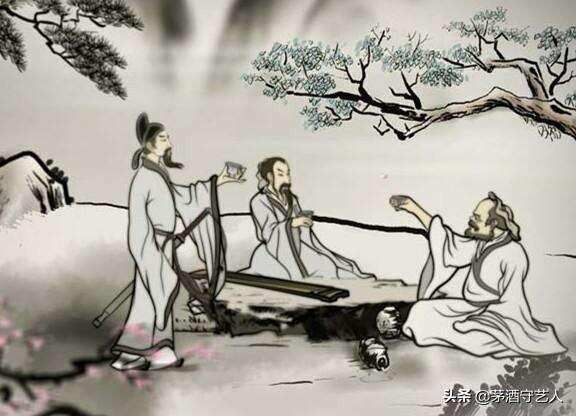
置身酒杯之外,面对醉酒之人的疯狂醉态,能够做到处变不惊,镇定自若的人自有其不凡之处。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