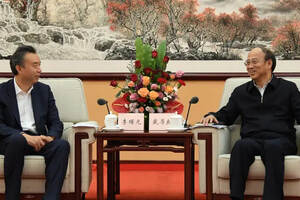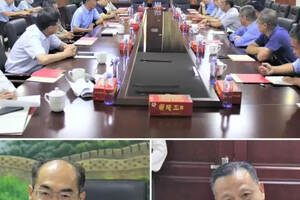放眼古今中外,好酒擅酒者难以胜数,而真正知酒乐饮,且形诸笔墨者,则属少数,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。
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女士携她的研究生杨早博士选编过一部《酒人酒事》(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),在辑一“何以解忧”所选的名家名文中,头一篇就是周作人的《谈酒》,在辑三“酒话连篇”中,有周作人的《谈劝酒》一文!在辑四“酒界往事”中,又选了周作人《我的酒友》一文,在同一本书中,收录同一位作家与酒有关的三篇文章,周作人是的一位。

夏晓虹教授(她来绍开学术研究会时,我曾与她同桌吃饭,有过短暂的交谈),在为该书所写的小引中,又再一次点了周作人的名:“现代作家对于各地酿酒业的贡献实在非同小可。不便说是‘一经品题,身价百倍’,但无论如何,文人的反复言说,确实积淀、造就了不同的酒格,赋予佳酿以深厚的文化意蕴。于是,讲到绍兴酒,就会想到周作人,提起北京大酒缸,也总忘不了张中行。而且,在这些文字的品鉴中,你分明可以读出绍兴老酒的文人气与北京白酒的平民味。”
我家祖辈与东昌坊周家曾经合族共居于周家新台门,若论辈份,周作人与我父亲同辈,比我只大了一辈。在兴房周伯宜门下排行老二。世人皆知周伯宜生了三个儿子,即老大周树人(1881—1936),小名樟寿,老二周作人(1885—1967),小名櫆寿,老三周建人(1888—1984)小名松寿。周作人此名还是我曾外祖父周藕琴的兄长周椒生(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监督)为他取的。其实周伯宜与其夫人鲁瑞一共育有四男一女。除上文提到的周氏三子外,还有比周建一点的女儿,小名瑞姑,不满周岁时因出天花患病而夭折。鲁瑞生周建人后又生一个儿子,即老四椿寿,惜6岁时死于哮喘病(肺炎)。据说周伯宜喜欢这个儿子,临终时说的后一句话,就是“老四在哪里?”椿寿病死时距其父周伯宜逝世不到二年。伯宜少奶奶先后失去了丈夫与爱子,心中十分悲伤,特地叫老二周作人请狮子街的画师叶雨香为老四画了一幅人像(其时绍兴尚无照相馆),裱成一幅小中堂,挂在卧房中,母子日夜相对。1919年,周家搬到北京后,此画也一直挂在老太太的房间里,整整挂了85年,直到1943年,鲁瑞去世,才取下交由周作人保管。我之所以节外生枝地写上这么一段,是为了替鲁迅家世做一点一般人所不知道的补充。

绍兴大户人家出来的人一般都会喝酒,都昌坊周家新台门里的人也不例外。祖父介孚公自不必说,父亲周伯宜平时一日三餐也少不了酒。周作人在《谈酒》一文中说他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,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,只记得他每次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,且喝且谈天,至少要花费两个钟头。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。都昌坊周家在周伯宜这一代已经败落了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每天喝酒的条件还是有的,周作人的舅父和姑父家里都是自己做酒的,整缸整缸的酒,自己喝不完,自然会按时按节送到城里来给至亲喝。周伯宜曾因其父的科场案被革去秀才的功名,一肚子委屈情绪,喝的自然是“闷酒”,他是属于真吃酒的那种人,不在乎酒菜的好坏贵贱。伯宜少奶奶也能喝点酒,但家务事多不常喝。周作人说自己很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,远不如其父与其兄,而且一喝就上脸,象个关云长似的,但喝酒的习惯与爱好,却从绍兴带到了北京。
1937年7月18日,周作人在北平写了《谈劝酒》一文,引乡人陈廷灿的《邮余闲记》与今人钱振鍠著的《课余闲笔》中的话,明确反对豁拳罚酒和强迫劝酒,认为主与客互酬,本是合理的事,但当有律度,要尽量却也不可太过量,到了酩酊酕醉,淋漓几席,那就出了限度,不是敬客而是以客人为快了。他还以其父周伯宜为例,说明对那些硬向人灌酒的人要坚守原则,不为所动:先君是酒量很好的人,但是痛恨人家的强劝,祖母方面的一位表叔喜欢酒,先君遇见他劝时就对不饮,尝训示云,对此等人只有一法,即任其满上,就是流溢桌上也决不顾,此是昔者大将对付石崇的方法。这对于今人如何应对那些“别有用心”的劝酒者也是一种启示。
周作人个性懦弱,常常屈服于人。他说自己不会喝酒而性喜酒,遇酒总喝,但他有自知之明,少醉酒,据说毕生只喝醉过两次,一次是教他《四书》的寿老先生请他喝酒,另一次是自己家里请人喝酒。
在《我的酒友》一文中,周作人说他有两位很好的酒友一位是沈尹默,另一位是钱玄同。喝的自然都是绍兴酒,沈、钱两位的酒量都不大,但酒德都不错。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,其中钱玄同晚年因为血压高,不敢再喝酒,为让酒友监督他戒酒,曾手书酒誓一张,交给周作人保管,发誓自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,对戒酒。钱氏说到做到,从此再也不喝酒。
周作人的文友与学生知道周作人爱喝绍兴黄酒,每次去看他时,总会带上几斤绍兴酒和花生米之类的过酒坯,而周也是来者不拒。但晚年的周作人牙齿残缺不全,花生米也咬不动了。他虽然喜酒,但更爱喝茶,便以茶代酒,招待故友。毕生舞文弄墨的周作人从不抽烟,也从不熬夜,总是早起早睡,饮食有度,生活很有规律。到80岁那年,身体还很硬朗,如果不是那场骤然而至的急风暴雨打乱了他在八道湾的平静生活,他一定可以活得更久。